 明信片,郵戳:柏林──施台格利茨,一九二三年12月23日
明信片,郵戳:柏林──施台格利茨,一九二三年12月23日致 米蓮娜‧波拉克
維也納 第七區
列興費德大街113-5號
親愛的米蓮娜:
要寫給您的信只寫了一段,放在這裡已經很久了,卻無法繼續寫下去。因為過去的煩惱又在這裡找到了我、襲擊我,幾乎又把我擊倒在地,我需要花很多勇氣,每一筆都很艱難,我寫下的所有的話,我都覺得很偉大,它們和我的力量較量著。當我寫下衷心的問候時,這問候很有力道地出現在那喧鬧的、混亂的、灰色調的列興費德大街上,在那裡我和我的一切都喘不過氣來,所以我再也不寫了,我等待著那更的或更糟的時刻到來。
順便一提,我在這裡受到盡善盡美又溫的照顧,我只透過物價上漲來體驗了解這世界,而且這是最震撼的體驗。我無法收到布拉格的報紙,而柏林的報紙對我來說太貴了,您可以偶爾寄些《民族報》的剪報給我嗎?用過往那種令我欣喜的方式。
這個住址我已經用了好幾個禮拜了──施台格利茨‧格魯那瓦爾德街13號,署名賽福爾先生。現在要致上最深的問候,如果它們才到花園門口就摔倒了,也許您的力量會大一些
您的K
註一:K,弗蘭茲‧卡夫卡。Milena Jesenska‧卡夫卡口中的米蓮娜‧葉森斯卡(Milena Jesenska)詳參維基Milena Jesenska一條,一堆死人尋我來我好累,不抄了。 好像還被拍成電影過,不過沒向吳爾芙那麼有名就是。
註二:這是卡夫卡寄給米蓮娜的最後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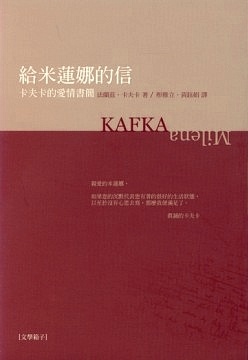
註三:據說這是米蓮娜和卡夫卡相識的咖啡館,現還好好活著。招徠行商走卒外,大概也引來不少卡夫卡迷或參拜或朝聖。畫中那為低吟黑衣女子決計不會是米蓮娜。

註四:Nigel Kennedy有個《Kafka》,和卡夫卡關係少點,和左岸咖啡館關係多點,〈solitude〉配唱廣告裡傳唱一時煩都煩死了。

書信之可以為文學,中外都有例可循。然而一般進入文學範圍的書信都在兩種情形下完成,一是寫信的人和收信的人當中至少有一位已經大大有名,片紙千金。因此他們往返的推敲討論,無不顯示率性之大義,自然天成,往往比正規的文學創作更加精緻晶瑩,甚至更加豐富深刻;一是寫信的人下筆時,即已決心把信寫好,寫得和他的一般的創作同樣講究,因為他知道百年之後,這些信難免會「流入坊間」,變成他文學成績的一部份,筆下須不可造次。文學史中這兩種書信都不乏實例,深為研究文學的人所鍾愛。除了這兩種之外,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寫信的人下筆的時候雖有抬頭稱呼,卒章時亦有再拜頓首字樣,甚至於轉折之間,也顯示出是為特定的人在寫,親切真摯有之,時時相互分享不可為外人道的秘密,以引起文體的特殊趣味,然而他知道這些信是「公開信」,馬上要發表的,所以嚴格來說,這已不是真正的「書信文學」,而是「書信體文學」了。
五四以來,第一類書信傳世的例子較少,能向濟慈的書簡那樣變成文學研究的瑰寶的,可謂絕無僅有;第二類書信較多,充斥於二流與三流文學趣味之間,這其中恐怕包括「兩地書」和「愛眉小札」。第三類──所謂的「書信體文學」──則不勝枚舉,是中國新文學的一大發明,利弊得失,見仁見智,非本文所能評論。而早期書信體文學中,亦頗不乏海外歸鴻一支,異國風光,情景交融,以生花渲染的文筆娓娓道來,自有其說服力和感動力,或寄小讀者,或在春風裡,美國心大陸尤其是令人缱而綣之的背景,稍微注意新文學的人,絕不會錯過這一方面的資料。
然而朱湘的「海外寄霓君」卻不屬於以上所舉三類之任何一類。(下略)
〈留學生朱湘〉‧台灣洪範《海外寄霓君》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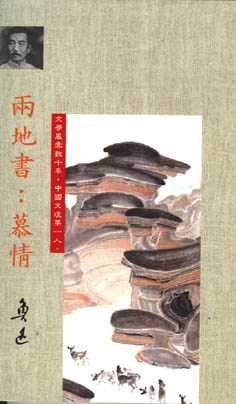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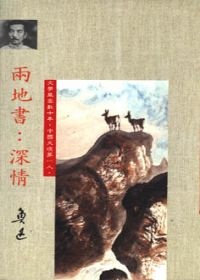

魯迅先生你有被點名哦!徐志摩天天到課就不算什麼了。
「皇天在上,我家祖先在上,朱湘如不守約,就天打雷劈。」(朱湘寄霓君‧信33)
「再提到丫頭片子,我將來是決不要的。」(朱湘寄霓君‧信46)
「將來我要是好一點,手頭寬裕些,我也是決定不會找姨太太這種禍根討回家的。」(朱湘寄霓君‧信88)

1.朱先生,屎可以亂吃話不能亂說,發這麼重的誓,保不定有個三岔兩短的你不尋小妾小妾自來尋你可怎麼是好?
2.討姨太太這種念頭是萬萬不能有的,都已經起心動念了,那討與不討又有差很遠嗎?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