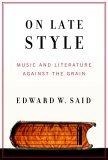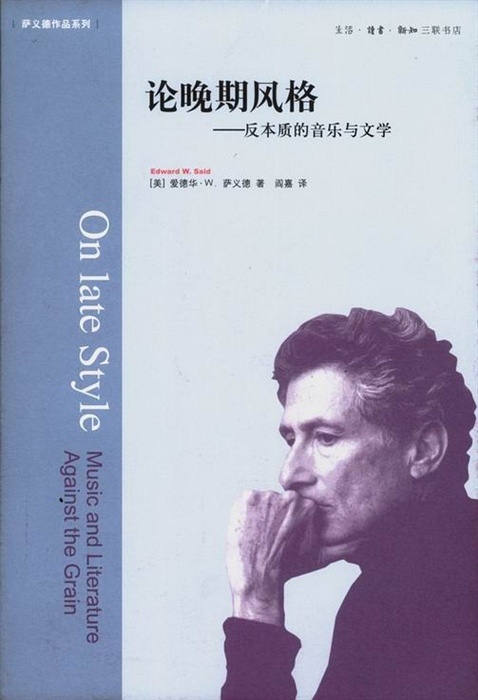薩先生的任何作品強烈不推薦給任何有後端消化系統困擾者如廁時使用,我雖不敏,至少束髮以來不論寵辱率多一跟腸子通到底的,讀到以下這段被薩先生的美文吸引也在legato上磨蹭繼而發呆一小時:
(前略)作曲家、演奏者、聆聽者形成的真實共同體——沒有錄音合約和大獎打擾那種——曾經視巴哈家族為令人心儀的模範,三者再度形成那種共同體的希望不大。大眾也不太可能變得比較不受誇大宣傳和商業主義影響。不過鋼琴界之內、之外都
有跡象顯示,很多人覺得有必要重新建立鋼琴演奏與人類及他活動之間的關係,好讓譁眾型鋼琴家那種不用心思的炫技能被真正有意思的東西取代。波里尼的成功當然和這種心理有關係,布倫德爾的成功也是。顧爾德的一切作為,都表達他對「彈鋼琴」這件事的不滿:他希望把鋼琴演奏和社會連在一起。
這一切都證明,鋼琴演奏正在嘗試衝出其知性上的沈默、其拜物性質、其「美麗的」聲音和炫技。我們永遠會佩服那些聲音、那樣的技巧;我們永遠會喜歡鋼琴家演奏標準曲目。但是,鋼琴的體驗如果和我們在其中獲得滋養的其他體驗連結在一起,將會更為濃烈。
鋼琴家如何使我們心動神馳,從演奏本身進入另一個意義境界?聽拉赫曼尼諾夫的錄音。拉赫曼尼諾夫令人興趣盎然;他的一切都使我們覺得他在介入一件作品,如果沒有他那樣的介入,那件作品只是紙上的死樂譜。我們覺得他想提出他的論點。家如他彈舒曼的《狂歡節》(Carnival),使我們感覺到作曲家在工作,作曲家使這件作品成為一種陳述;但是,舒曼那種十分私密的靈見是混亂的,那混亂在拉赫曼尼諾夫掌下流露無餘。柯爾托的彈奏也給我們同樣的感覺。
這樣的琴藝不只是敢冒險,彈出奇快的速度,引入抑揚劇烈的旋律線。應該說——這是核心要點——這樣的琴藝將我們拉進音樂裡,因為其過程明顯、令人情不自禁、可解而發人深省。同樣這個要點,也有可能變成負面的東西。有一種鋼琴家他關切的唯一事情是完美,完美到我們說:這演奏多麼完美。比賽得獎的風氣的確助長一種「成就」美學,除了鋼琴家令人眼花撩亂的指法,演奏裡什也沒有。換個說法就是,有些「完成度」極高的演奏(我想起約瑟夫‧列維涅)變成只是彈琴,把聆聽者推開了,鋼琴家與人隔絕,獨自留在只有「職業演奏家」活得下去的荒涼環境裡。
能鼓舞我的,是那種讓我進去的彈法:那種使我覺得我也要向他或她那樣彈的鋼琴家。把莫札特和蕭邦彈得純粹灼人的李帕第(Dinu Lipatti),就給我這樣的感覺,名氣沒那麼顯赫的英國鋼琴學派——哈絲(Myra Hess)、柯爾榮(Clifford Curzon)、偉大的索羅門(Solomon),以及與他們在伯仲之間的莫伊塞維奇(Benno Moiseiwitsch),也流露這樣的境界。今天傳承這香火的是巴倫波因、魯普(Radu Lupu)和普萊亞。
你也可以主張說,鋼琴演奏的社會本質和我說的這一點正好相反,說他
應該疏離大眾、和大眾保持距離,以便產生炫技鋼琴家的那些社會矛盾更為強化,而這就是當代文化過度專門化的一個後果。不過,這個論點忽略了一同樣明顯的一點,而且也是消費主義所產生的疏離造成的——也就是說,鋼琴演奏的
烏托邦效應。演奏者往來於作曲家和聆聽者之間,演奏者的演出只要吸引我們參與演奏的經驗和過程,也就是在邀引我們進入一個知覺便銳利的烏托邦情境,我們在別處是享受不到這種情境的。簡而言之,
吸引人的鋼琴演出能夠打破觀眾與詮釋者之間的藩籬,而且又不侵犯音樂的寧靜本質。
一場演出如果打進觀眾的主觀時間,豐富那時間,使那時間變得更複雜,這演出就不只是兩個小時的賞心樂事而已。我想,鋼琴和鋼琴家令人感興趣的本質就在這裡。每個聆聽者光臨一場演奏,都帶著別的演奏會的記憶而來,那是這個聆聽者與音樂的關係史,一張關係之網;這些全被眼前這場演奏啟動。每個鋼琴家啟動這關係史和關係網的方式都不一樣。顧爾德似乎不斷在發明一個新的他和新的彈法,他彷彿沒有來歷似的。對為法好像直接、生動、以可解的語言對你說話,強迫你暫時擱置你的觀念和時間。波里尼彈舒曼,則讓你不但聽出舒曼的長短句天才,而且聽出別的鋼琴家來——例如米開蘭傑里:波里尼學益於他們,然後另闢新境。這兩位鋼琴家都具備知性的嚴謹,其強度與說服力像極了第一流論說之作的文字。
最偉大的鋼琴家就這樣擔任接通兩個世界的橋樑:一邊是演奏台那種至精至純而不自然的世界,一邊是人類生活中的音樂世界。我們的確都曾受到一件音樂作品的強大感動,並且想像自己不得不表演那件作品時,大聲表現它,一個音符一個音符、一條線一條線為它發音,是一種什麼滋味。最好的鋼琴家就是能夠刺激這樣的經驗:他們的彈法的說服力、他們的聲音之美和高貴,使我覺得如果我能像他們那樣彈,可能會是何等感覺。
這完全不是說,一位演奏者符合我們的期望。正好相反:這是說,一位演奏者引起期望,使我們和記憶相會,那記憶只有此刻眼前這樣演奏的音樂能夠表達。
多年前在法國,我聽偉大的德國鋼琴家肯普夫演奏。就我所知,肯普夫晚近只在美國演出一次,是十二年前在卡內基,並非十分成功。他在美國受到的讚揚不多,或許被巴克豪斯(Wilhelm Backhaus)和塞爾金等不如他的同世代人蓋過去了。肯普夫的音樂有其獨一無二的,歌唱般的音色,他的彈法有個層面和顧爾德一樣不尋常,就是沒有帶著他師從過的老師的印記,也沒有其他鋼琴家的印記。在他的彈奏裡,你聽見一種逐漸披展的詮釋。在肯普夫,技巧是為發現服務的,鋼琴是一個塑造知覺的工具,而不是發出時髦聲音的道具。他彈一切作品,從貝多芬作品110號末段賦格的嚴謹對位法,到舒曼《克萊斯勒魂》(Kreisleriana)的奇幻氣勢,都是如此。
肯普夫的彈法並不自以為是,也不以力道給人印象,但我們感覺到他在實現他對音符的解讀,很像我們在一段漫長的時日裡學習一件音樂作品,逐漸了解它,終而——套用一個漂亮的說法——「會之以心」。
要明白我說的意思,請聽肯普夫1976年演奏的巴哈〈耶穌,世人渴望的喜悅〉(Jesus, Joy of man's desiring),大多數人對此曲所知,是來自李帕第透明、純淨的錄音。不過,李帕第使用哈絲的改編,肯普夫用的是他自己的改編版,因而提高了他演出的親切韻味。巴哈此作在靜穆中闡釋聖詠曲旋律,配上波狀三連音伴奏,李帕第使用圓滑奏,其中蘊含了完美發抒的內聲部;這樣的表現法,大多數的鋼琴家十分欣羨。不過,聆聽者總是知覺到有某種效果在要求他注意,李帕第的詮釋與肯普夫的詮釋比較的時候,這一點特別明顯。肯普夫到達聖詠旋律的最後陳述時,三連音伴奏和旋律的境界已經擴張了,大到這位鋼琴家畢生致力巴哈音樂的工夫精華盡含其中。這嚴整的演奏提出其結論,沒有虔敬的勝利姿態,也沒有已經成濫調的那種憂鬱。這件作品的外在證據和內在運動,我們體驗起來成為共同發音的兩個形式。我們領悟到一點:我們透過彈琴(如果我們會彈琴)和聆聽所知道的鋼琴演奏,雖然發生於公共領域,其最完足的效果卻是在聆聽者自己的回憶與聯想這個私領域感受的,一方面是演出、品味模式、文化機構、美學風格和歷史壓力,另一方面是遠更屬於個人的快感。
我說這話,想提的是普魯斯特在《追憶逝水年華》(A le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和托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裡探索的那種可觀的音樂世界。這兩部作品是文學、音樂和社會三方面的現代主義匯集而成的巨作。顧爾德好像是托馬斯曼筆下那位雷維庫恩的化身,阿圖‧魯賓斯坦剛健的琴風則好像直接來自普魯斯特筆下蓋爾芒特家(Guermantes)的沙龍和音樂會,凡此都顯示這三個領域在今天仍然多麼有力互動。
企業經營的音樂世界取代了波西米亞和上流社會,成為音樂會環境,沒錯,這裡面有商品行銷,不過,其中也見證當代鋼琴家致力使之高貴的一個傳統,當代鋼琴家每次達到波里尼的水準,都是在證明這個傳統的多彩和嚴肅。
最偉大的演奏能夠提供散文那種無比珍貴的陳述和有力的詮釋;散文是一種光輝被史詩和悲劇的宏大結構掩蓋的文學形式。散文如同獨奏會,是偶發的,也是重視再創造,而且個人的。散文家,如同鋼琴家,以既有的東西為素材:那些藝術作品永遠值得再來一次嚴謹、帶著反思的解讀。最重要的一點是,鋼琴家和散文家都不能提供最終底定的解讀,無論他們的演出多麼給我們一件事有了「定義」的感覺。這兩個類型在根本上都有一種輕便(sportiness),這種輕便使它們維持誠實,以及保持活力。不過,鋼琴家的藝術另有一種根本的傳奇味道。舒曼《幽默曲》和蕭邦F小調敘事曲裡潛藏的憂鬱;名字彷彿帶著魔法的傳奇鋼琴家——布梭尼、達貝特(Eugen d'Albert)、李斯特、戈多夫斯基(Godowsky)——歷久彌新的權威;那種既能含蓋最紮實的貝多芬,又能含蓋最纖細的佛瑞的音響力量,以及獨奏會氣氛裡流動的那種專注奉獻和金錢氣味:凡此種種,都向我們訴說著鋼琴藝術的傳奇境界。
〈追憶鋼琴家的台風和藝術〉

這篇文章前半還有一大段討論鋼琴家組織曲目的行為意義,有趣又牽涉到很多鋼琴家作曲家的風格問題,我就不再引了。我很喜歡看薩先生音樂文本以外的批評,這裡指的是他出入於文學音樂之間龐徵博引、無視那些幾已形成「傳統」或定論的意見,直探演奏行為本質與內在。遇到他目為腦殘的演奏者則不免誚直深刻毫不容情,而他推崇的演奏者如顧爾德等,卻總能挖掘出前人未見的內裡,看了很過癮。接著我還要看《論晚期風格》的繁體中文譯本,這本薩先生的天鵝之歌我讀過英文版、簡體中文版,英文版本來就跟天書,簡體版譯文失之枯澀,很高興見到繁體中文版還是彭淮棟先生操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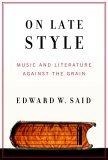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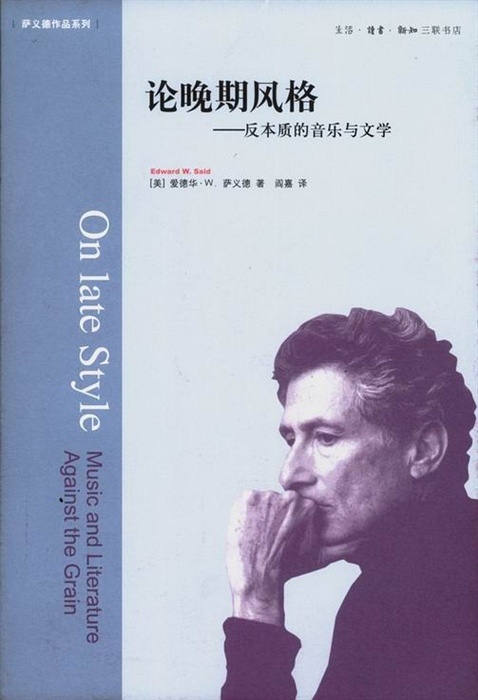
謝謝奧菲斯小姐找到彭先生這樣信實而有文采的譯家匹配讓我閱讀中文版多了很多樂趣。至於書介上說到「霍洛維茲是尖銳刺耳風格的代表?」「美國大都會歌劇院盡上演些二流劇目?」雖然有部分真實性卻不免有斷章取義之嫌,遠非薩先生整體格局視界所欲闡發之萬一,看看就可。
還有,這本書擺脫了莊秀欣所瘋狂推動的部編本統一譯名的幽靈,誠可喜。妳又不拿他廣告贊助,管他發神經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