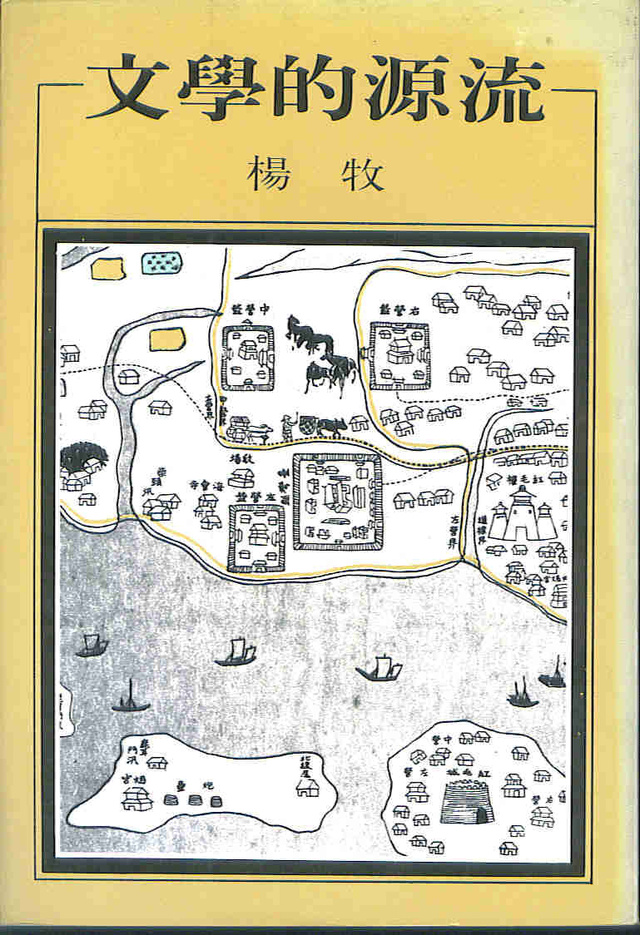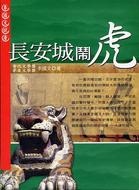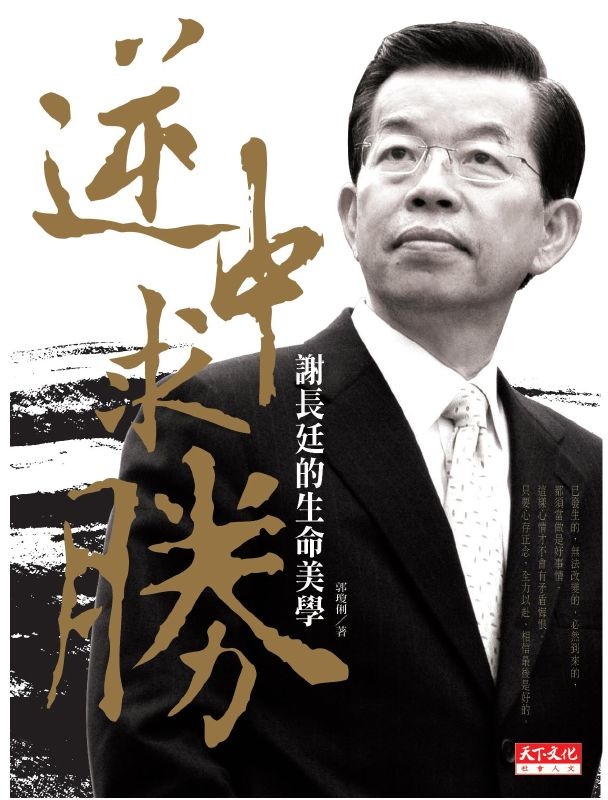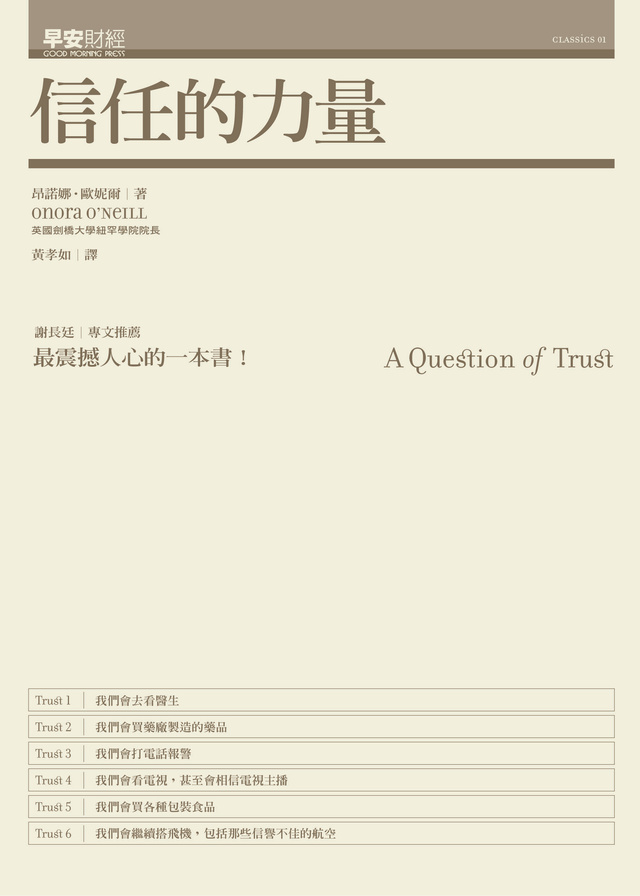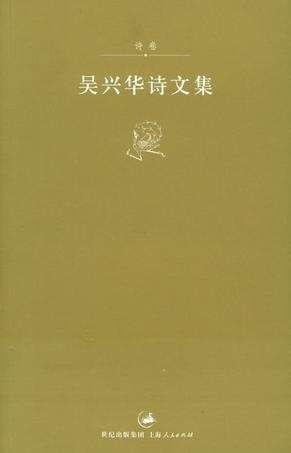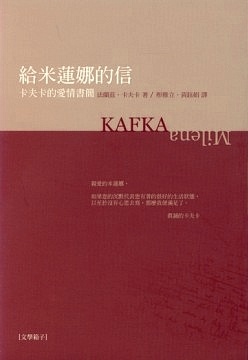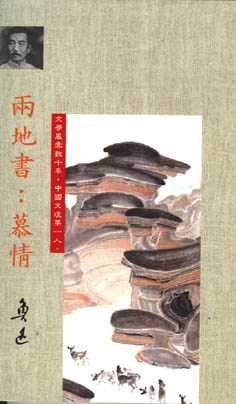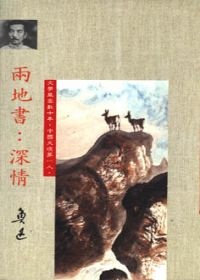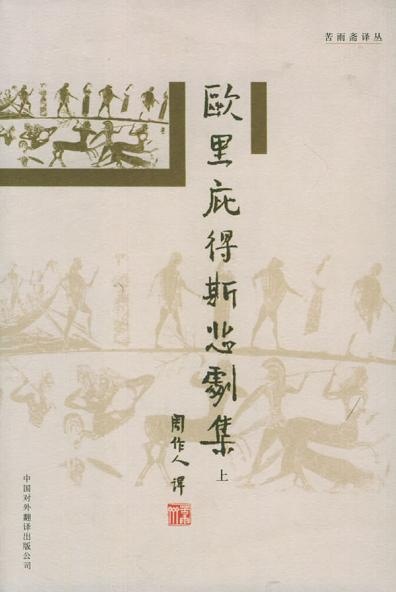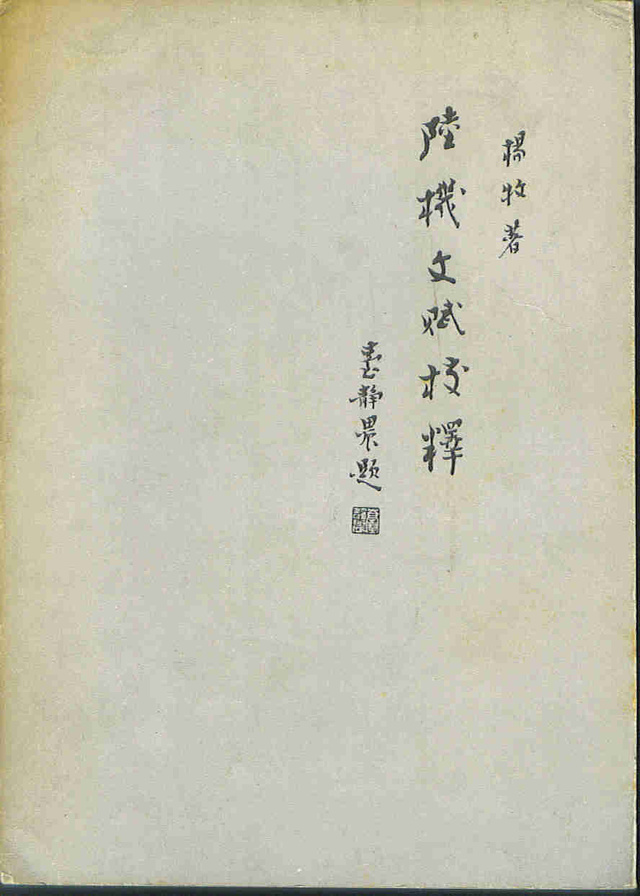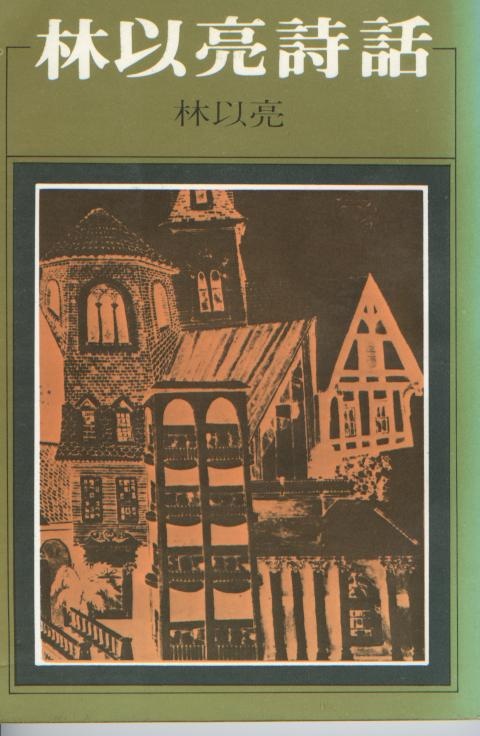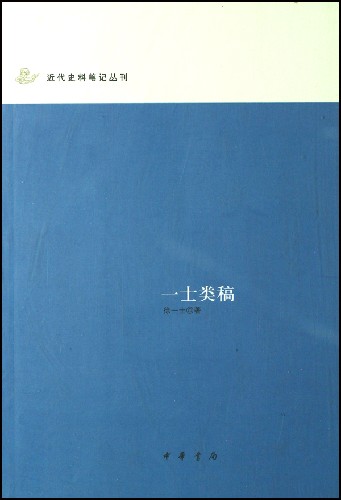應Ronja之請這裡也給貼一回〈翻譯的事〉。
這篇講稿還沒看到收錄在哪本書,原載2006年12月6-8日聯副,編輯按語提到是年楊牧返港科大客座對該校學生的一場講稿,說是翻譯其實講的更多的是前代學人林以亮和詩人的香港因緣。《談文藝憶詩友》有一大篇寫的除了何懷碩其他都早列仙班,有一章就講林以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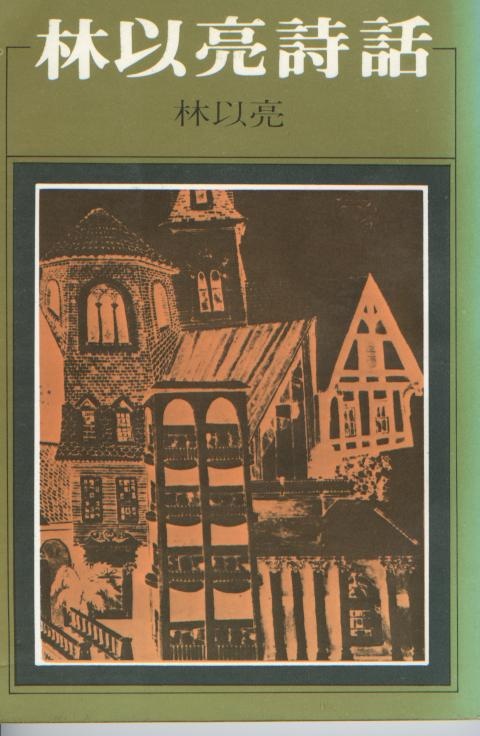
翻譯的事
楊牧
六十年代中我因為偶然的機緣認識了林以亮,想起來就是在愛荷華第一年結束的暑假。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他去世為止,三十年間維持著極好,親近而溫馨的友誼(我這樣想是不會錯的,回憶起他長時間裡對我的期許),雖然只見過少數幾次面。他寫了許多信給我,繞著讀書,創作,和翻譯之類幾樣事情談論著,商量著,偶爾月旦或存或歿的人物,此外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話題,但他又時常提到自己怎樣就生病住院,甚至開刀服藥而終於無礙痊癒了,適可而止,筆鋒一轉又回到讀書,創作,和翻譯。我說我們認識了,就是說那長期通信關係的開始,而這其中感受到的累積的感情反而就十分沉重,尤其是現在,離開他去世也有將近十年的時間了,並沒有使我忘懷。
我記得他最初是接受聶華苓的推薦,邀我參與翻譯一本書。這本書後來在香港出版了,就是《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譯者有林以亮,張愛玲,於梨華,和我。翻譯篇數最多的是張愛玲,計有關於小說家的文章三篇和原主編者的序文一篇,其次於梨華和林以亮各一篇,我兩篇。張愛玲譯的序文,原撰稿者威廉‧范‧俄康納(William van O'Connor)是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文筆精銳,劍及履及。記得首頁翻開就有一則關係著作者相對於小說主題的論述,被她這樣毫無保留地轉化呈現了出來:小說家「不應當預先知道他的題材的意義。他必須等待故事開展,逐漸發現他的主題。如果這本書寫完以後,主題極清晰地出現,那麼作者大概是隱匿了一些證據,寫出來的是一套教訓或是宣傳品」。
林以亮指定我譯的兩篇,一篇關於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另一篇則為拿撒奈‧韋斯特(Nathanael West);前者原文執筆人也是俄康納。那暑假我住在舊金山灣區的柏克萊,每天規規矩矩坐在樓上窗前,設法把嚴謹的學術論文譯成中文,也沒有什麼參考書,因為到那時為止,我只讀過一本福克納的原著《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和少數短篇小說如〈熊〉("The Bear")等,而韋斯特更從未曾聽說過。一個外文系畢業的人尚且如此,這其中有些諷刺的意味,但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文學是需要翻譯的,而外文系的人就理所當然應該去做才是。林以亮為早年燕京大學西語系出身,內戰末期到香港,主要就是從事西書的翻譯和電影編劇,到我們通信的階段,他已經是朋輩中有名的「翻譯先生」(Mr. Translation)了。所謂朋輩,就是他有一次忽然在信中對我提到的,「同我差不多年齡的友好,如姚克,張愛玲,喬志高,蔡思果」等四人,都為衣食忙,他說,致未能專心文學,接下去就感慨地講了些自覺「蒼涼」的話。那當然也是長久以前的事,遠在我能完全領略其中的感慨之前。此後數十年,他曾經屢次提到些時不我與,深怕理想的工作未能完成等自我警惕的話,都使我矍然心驚,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原來他的身體情況一直不好,長期帶病養生,遂有許多恐懼不安,因此更傾向在信中多談他寫作和編譯的計畫。在我這方面,林以亮對翻譯一事的熱衷和他對我的期待,竟有意無意為我點出了一條值得試探的路,一片於學術或創作都有可觀的新領域,充滿了信念,遠景。
回想起來,在為林以亮譯福克納和韋斯特兩長文之前,我可以說從未曾真正嘗試過翻譯。有則在大學時代私密的練習,而我記得的卻是一件頗具野心的計畫,和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最純淨,透亮,而不減絲毫繁美的神話與詩有關。就是在東海畢業前一年吧,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就動手開始翻譯起濟慈的長詩《恩迪密昂》(Endymion)。這首詩原文分成四卷,全長超過四千行,以英雄雙行體為基調,在嚴謹中賦予浪漫的氣息,所以頗具有一種無韻體的聲色,在英詩中也屬源遠流長:
美的事務是永恆的歡愉:
其可愛日增,不消逝於
虛幻無影;反而就長久為我們
維持一座靜謐的涼亭,為睡夢……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
Its loveliness increases; it will never
Pass into nothingness; but still will keep
A bower quiet for us, and a sleep ……
我確定至少翻了一千餘行才停,手稿還在篋中,包括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的前七十九行,就在那關口戛然中斷,原因不難想像,只是當時已惘然。我最後那幾行約莫如此:
當微風奏出一支甜蜜的聖歌
去取悅德俄菲的時候,就有雪白輕快的
節奏溶進無聲的靜寂。他的兩腳急促
依然在這輕翼的引路人下飛跑……
濟慈二十二歲動筆寫此詩,不及一年脫稿,出版時書前印了一自序短文,懇切希望讀者諒解其中「可能暴露的生疏,不成熟,和錯誤」,果然,濟慈為了這首少年心血烙印的「詩之傳奇」(poetic romance),很快就遭遇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和攻擊。我奇怪的是,為什麼我自己也挑了這樣一首艱深而不祥的長詩來譯,在那青澀的年代。中斷的四句如彼,甚至原稿所保存的第一卷開始四句亦復如此:
美的事務是永恆的歡愉,
它的可愛日增,永不消逝;
恆久為我們保有一個
無聲寧靜的園亭,又像那……
這其中恐怕更暴露出譯筆的「生疏,不成熟,和錯誤」了。越過大段的歲月回顧,何嘗不慶幸當初的努力知所停止,功不唐捐,猶不免惶惑之至。除此之外,記憶裡還未曾翻譯過任何別的東西。所以我總是耿耿於懷,的確是林以亮點撥了我偶爾試探這另一支筆的興趣,在人生旅程的徬徨,摸索中。
那一年暑假順利譯畢福韋二文,回到愛荷華,冬天開始選擇卡謬(Albert Camus)的札記,取其文學與哲學以及一些關於社會文化的思維,逐日就其英譯本而轉譯,自以為興味盎然,例如:
革命,光榮,死亡,愛情。比起我內在那些沉重又真實的東西,
這些名詞有甚麼意義?
「而那是甚麼?」
「這淚水浩蕩的重量,」他說:
「便是我所了解的,我所體會的死亡的滋味。」
例如:德國人發明了自鳴鐘。這種東西是時間之流的可怕象徵物。那宏亮的鳴聲在西歐無數大城小鎮日以繼夜地響著,而且那也許最有力地表現道:「以歷史意識面對世界乃是有利於創造的。」
同時,就在那冰雪嚴封的冬天,我開始以一種責無旁貸的態度埋頭翻譯西班牙詩人羅爾卡(Federico Garcia Lorca)的吉普賽謠曲,出版時取名為《西班牙浪人吟》(Romancero Gitano)。這本詩集先由我一手自英文轉譯,但心中不安,我請一位懂西班牙文的朋友坐下來和我一起檢驗其信實。我將我的中文稿口譯回英文,由他當場比對手上的西班牙文,希望不至於太乖離原作,有則即刻討論更正。
所以我說翻譯的事,真正有個開端的話,痕跡確實在林以亮派給我的那暑期工裡,後來才緊跟著做了少許一些零星的事,但還是有限。當時林以亮並不是把我分內的材料指定就罷。我交稿後,他顯然很認真地審閱了一遍,提出疑點,以討論的口氣建議我是否修改,怎樣修改等等翻譯者經常遭遇的問題。韋斯特一文寫到小說家上了布朗大學後頗能孤芳自賞,變成一個衣著入時的大學生,身穿Brooks Brothers考究的外套和襯衫,頭戴漢堡呢帽,同學形容他就像個「相當有錢的殯儀館助手」。我把那時代的名牌衣服店,即曼哈頓的布魯克氏兄弟公司誤解為一般美國大學生的兄弟會之類組織,被林以亮發覺有誤,及時更正。他的耐性和細心常使我覺得很感動,寫信的時候我就維持著最嚴謹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如此,稱呼他「以亮先生」。一九七三年他和高克毅合辦《譯叢》半年刊於香港中文大學,那幾年我專致於二十世紀初葉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研究,不久就針對周作人和希臘文學的關係在深入閱讀著相關的書。林以亮知道我肯把古典希臘和現代漢文學的題目這樣連結起來,非常高興。有一天我收到一大包書,打開一看,才知道他特別為我從朋友處借出,迢迢自香港航郵寄來的《希臘的神與英雄》,《希臘女詩人薩波》,和他自己收藏的《伊索寓言》,皆周作人五十年代初期所譯希臘文學的珍本,竟原書渡海,還附一信云:「書我既已借來,可暫時存兄處,不必影印,俟論文寫竟後再寄還不遲。」不久寫竟的就是後來發表在《譯叢》的英文論文"Chou Tso-jen's Hellenism"。此文從屬稿到排版付梓,得到他和高克毅兩位往返琢磨討論,使我獲益最多。
林以亮那一次提及他同時代的友好共四人,其中高克毅、張愛玲,和蔡思果我前後都見過。但我知道和他年紀相當在海外的友好,至少還有陳世驤和夏志清,沒提到是因為後兩位都在大學教文學,研究文學,不在他感慨須分心「為稻粱謀」的範圍之內。按上文林以亮想起他自己和那四位朋友,頗覺「蒼涼」,似乎誇張,但那可能就是最正確,最保守的兩個字。夏志清研究張愛玲,認為她小說力求表現的無非「蒼涼」;這一方面鄭樹森考之甚詳。林以亮生前談到二十世紀的新詩人,必舉吳興華,認為是那一輩中翹楚,其他人都比不上。他考證吳的生卒年代大概是1921-1966,屬文革最早被整死的知識分子之列。吳死後,林以亮將他的遺作四處發表,一部分就寄夏濟安,登在台北早期的《文學雜誌》上,刊過一篇〈論里爾克的詩〉,作者署名鄺文德,及若干直接譯自德文的里爾克詩選,都是他提供的,而鄺文德正是他為吳興華取的另一筆名。早在抗戰時期吳就已經以本名為中德學會譯過一冊《里爾克詩選》;又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林以亮夫人名鄺文美。
張愛玲於六十年代晚期到柏克萊任職於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為研究員。研究中心也是大學一部分,其中有一特別單元稱為「當代語言計畫」,主持人一直是陳世驤,早期獨當一面的研究員即夏濟安。我初到柏克萊那年暑假,陳先生要我以助理的身分整理夏先生遺下的卡片箱,就坐在那間老研究室裡東翻西翻,其實並沒有什麼意思,只是過目了許多新中國稀奇古怪的宣傳口號或批判語彙之類,一直到秋天開學,就不做了。中心後來正式聘莊信正為計畫研究員,越二年莊辭職去洛杉磯就南加大教職,陳先生不聲不響請來了一位女士繼任這件工作,就是張愛玲。我第一次見到張愛玲的時候,其實從來還不曾讀過她的小說,但我讀過夏志清的英文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其中闢有專章研究她,何況我們曾在林以亮的主持之下,合譯了一本《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所以就趕快去找她的小說來看。現在想想,那時張愛玲大概也才四十多歲,但幾乎所有她到今天還有人讀的小說都已經寫好了。張穿著很樸素,記憶裡總是那樣安靜端莊地坐在那裡,不和人家搶話講,只專心聽著,點頭,好像沒有太多表情,雖然偶爾臉上也露出同意,欣然的笑容。
張愛玲記得我為那本美國書翻譯的福克納和韋斯特,稱讚了幾句,很驚訝我原來還是一個剛起步的研究生。有人問她關於〈傾城之戀〉的事,她支吾不願意談;又問七巧,也同樣無心深入的樣子。那之前,我們來自台灣的同學都讀過一本不知道怎麼從日本流到北美的打字印刷,非正式出版的《今生今世》。有人於是不懷好意地想試探這個題目,但她把頭轉到一邊,面無表情。我不知道她在中心的工作是否即夏濟安一路下來的延續,但那一兩年文革方熾,我們關心中國現狀的人課後常到中心的圖書館看報;我去時通常是下午暮靄遲遲的時候,屢次遇見張愛玲剛進中心大門,互相禮貌地招呼,隨即看她安靜地穿過長廊,走進她的研究室。照中心慣例,研究員一年須提出一篇具有分量的論文;但那一年度未完,陳先生就去世了,所以我們都不知道她的論文怎樣。據說那一天晚上陳先生的追思會中,張愛玲其實也是在座的,但我沒有注意到;又據說會未終了,她就起身在簷下獨立,逡巡,而終於悄悄地走了。
而就在這樣一種暗澹,逐漸微弱的光影裡,我們的六十年代就幾乎無聲息地隱入勢必的記憶,忽然的和累積的,未竟的音訊,情節,故事,無法重組的美好和不美好,都將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偶然浮現,提醒我們蓄意編織的夢,破碎的夢,消滅虛無的夢,歸根究柢終於是真實的,曾經都將在此後侷促的歲月裡,轉化那具象的真實為更高層次的神情體驗,在文字的驅遣,複沓,重疊,和離析等等這些大動作裡,這些藝術結構的訴求裡,找到我們的思維藉以詮釋的端倪,發現生死歸宿何其渺茫:愛若是蜉蝣短暫,恨何嘗不是?愛和恨的時代,風雲和煙雨的時代,殘忍,同情,我們的六十年代,革命和禪修,抗議和出賣,無數影象猶栩栩在記憶裡有機地滋生,慾望和仇恨,映向空白的期嚮,紅杉巨木的針葉在窗外搖擺,窺探,古典文本在燈下,獼猴桃在冰箱裡,香菸在床頭,家國在失眠的晨星一再重複的水瓶,金牛,和處女座,稀薄的音訊裡未竟的音訊,失←,監禁,死亡。何其失望,何其悲傷,何其莊嚴而浪漫。
七十年代中,有一年端午節我去香港,住在薄扶林道朋友家,才發覺這其中有一種無可抗拒的異國情調,如此強烈地吸引我,廣大深沉的港灣,更遠更遠異樣的水平線,和我從窗口俯視的住民,安靜的,熙攘嘈切的人車,使我精神為之搖動。這樣真確的異國情調,包括那可愛的語音,甚至在美國或歐洲都未曾經驗過。我第一次和林以亮見面時,感到人群中他如何表現出一種對我特別接納,親切的神色,深怕別人不知道我們關係多麼不比尋常,通了許多信,在一般的文學修養範圍內幾乎無事不談。同時我也感覺到他其實是一個驕傲的人,至少對某些人說來,甚至是不可親近的。他對我說陳世驤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正在新加坡,聞訊全身顫抖,久久不能自已;我記得我也有相似的反應,在麻薩諸塞州被電話喚醒的子夜,前未曾有的經驗。他問我的寫作和研究計畫,家庭情況等等,又突然問我練過字沒有,於是就談碑帖源流異同,非常深入,許多都是我不見得理解的。後來回到台北,我就接到林以亮寄來的一包書法碑帖,原來他是覺得我的鋼筆字顯然欠缺了甚麼規矩之類,必須加以約束,就為我進城去挑選了這些書法範本,要我定下心來拿毛筆勤練習之。我很感動,但練字實非始料之所及,所以又延宕良久,有一天隨意在書堆裡拿出一本《道因法師碑》跟著寫起來,一匝月即止,未再寫過。
我聽說林以亮和早期香港的電影事業很有關係,曾擔任過幾個大公司的製片和編劇,而他和張愛玲的交情大半際會於此。六十年代張曾為電懋寫劇本,其風格即受林以亮早出的喜劇《南北和》的影響,而且她筆下的粵語對白一向須由林以亮修改才定稿。然而相識那麼多年,我並不曾看過他在信裡談及電影這個題目。但我也記得當初他為我譯韋斯特一文改稿時,進進出出特別精細準確的是關於韋斯特在好萊塢編劇之始末,有些習慣用語若不是他為我釐定,恐怕就錯誤百出了。他八十年代好像都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校長特別助理;我可以想像他依然故我,愛才不吝施捨,絕無保留,甚至到了護短的程度,但又不願意含糊以敷衍平庸,也就是說,原來那一份知識之傲氣總是不少的,所以我在香港遇見的人當中,對他不以為然或談起來就咬牙切齒的,似乎比對他傾心致敬的人更多。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到香港參與科技大學創校,那時林以亮已自中大退休,平時在家看書養病,或提供諮詢資料給《譯叢》編輯同人。秋涼時,經過多次要求,他終於答應讓我前去拜訪。記得他家在一個叫「嘉多理山嘉多理道」的陂陀多樹的社區,甚為幽靜。林以亮坐在起居客廳的大椅子上,侃侃而談,或立起走到書架前取物示我,精神相當不錯。告辭出來,回頭揚手作別的時候,才感到他那清渥的病容,以及更明顯觸動我內心的,他多麼捨不得我們這樣匆匆來去,依依的表情,在南國晚起的秋風裡。
林以亮去世時,我已離開香港若干年,而在這之前,因為健康和際遇的關係,他的信也寫得少了,來往香港的朋友都不清楚他的情況,問也問不出道理來。等到證實他已溘然長逝,大概就是一九九七年暑假之後了。林以亮身體一向不是最好,長期都在就醫服藥,甚至屢經外科手術,堅忍養護,還做了許多有功於文化的事。對個人而言,他期許激勵於我的正是文學的創作和學術研究,授受之間何等慷慨,大方,且不遺餘力,以及我偶爾奮起從事的翻譯工作,其實正是他給與我的啟發。雖然,我還是不免遺憾,當初選譯葉慈詩得以成書出版已經是一九九七年了,但早先工作開始的時候我還住在清水灣,竟未能就近讓他看到一些稿本;至於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想必是他最感興味的題材,無論就他超越的家學或人生體驗而言都是,但也來不及了。
翻譯的事固然是我的「香港因緣」的開始,也在那長期的接觸和實習裡逐漸能以真心看待這件事,甚至有了些理論的認知———這是香港給與我的賞賜。而在個人心懷之中,我也時常覺得,當我認真工作,從那嚴謹的聲韻結構和主題觀念中追究詩的神髓,嘗試以現代漢語加以表現,力求完整,我紀念著林以亮,所以那些微薄的成績或許就可以看作是為報答香港而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