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如一位作家,不作文,只作秀,久而久之,讀者只記住了他的秀,而記不住他的文一樣。
〈奇怪的贓物——胡椒八百石〉‧長安城鬧虎‧頁16‧李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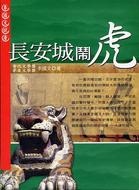
......。志清為學博大精深,當然是主流中的砥柱。他再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了以儒家為主、以佛道為副的中心思想。在評論作家和文學作品時,他著重的不是技巧、象徵、神話等表面上的情節,而是作品深處的「感時憂國」和「悲天憫人」的人道精神。儘管他對《紅樓夢》有極高的評價,他仍不免喟嘆:「大觀園實在是多少小姐、丫鬟的集中營。」儘管他認為《金瓶梅》「把那時代『非人的』社會和家庭生活寫得透徹」,他卻引用了現代美國女作家Katherine Anne Porter的話:「《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描寫的生活無非是一連串灰暗單調的日子,偶然給一次性交所調劑。」然後指出:「如果這段描寫對勞倫斯的小說太不公平,大可用於《金瓶梅》上,當更為適合;可是西門慶一家所過的日子,非但沒有給經常出現的性慾上的火爆場面所調劑,反而變得更沈悶乏味。」(下略)
〈秉賦‧毅力‧學問——讀夏志清《雞窗集》有感〉‧更上一層樓,頁81‧林以亮

其實,性乃人之本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不必諱言,也不閉將那兩個器官,整天掛在嘴邊。但人類與動物的區別,正是在於對這種原始本能的掌控上。控制得住本能的白行簡,堂堂正正地在他的這篇《大樂賦》署其真名;而控制不住本能寫《金瓶梅》的那位才子,深知自己連篇累牘的猥褻筆墨,下流描寫,其不堪入目,其過份骯髒,與動物發情無異,才把真名隱去,用一個「蘭陵笑笑生」的筆名,遮住那張大概有點心虛尷尬的面孔。
魯迅先生批評《金瓶梅》的性文字,「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認為幾近病態。其實,那不是病,是荷爾蒙作怪。
當代作家中,熱衷此道者,屢見不鮮,寫著寫著,就寫到褲襠裡去了。可以諒解的是,在當今物質至上、人慾橫流的環境中,聲色犬馬、酒醉飯飽的作家,出現這種動物式的發情衝動,也是順理成章的必然。
〈中國色情文學的開山作——白行簡與他的《大樂賦》〉‧長安城鬧虎‧頁110‧李國文

......。楊(慎)和袁(枚),為名清兩代文壇上的重要人物,但聲名並不十分令人起敬。他們多少向玩票一樣,穿上戲裝,過一過古人的癮。這也是中國文人中較為低劣的行徑,尤其是沒有什麼本事,沒有什麼能耐的文化人,更熱衷於假託古人,偽造古籍。
君不見一部《紅樓夢》乎?直到今天,仍舊被一幫老的少的蛆蟲們,弄得天翻地覆嗎?今天發現故居,明天早到墓石,大前天挖掘出脂硯齋。大後天很可能通過DNA查出曹雪芹的遺腹子的遺腹子,現在為大名鼎鼎的紅學大師云云。這種搭順風車,這種借古人之光,這種花不大的力氣,蟻附於前賢而混跡於文學史,這種裝神弄鬼,作偽造假,借殼上市,魚目混珠的種種名堂,成了他們手淫自瀆成癮,難忍難耐難改的惡性病癖。
〈中國色情文學的開山作——白行簡與他的《大樂賦》〉‧長安城鬧虎‧頁116-7‧李國文
抄得累死了,也總算抄到入港了。
我先宕開一筆,王月曹蘭附身一下說個生活小智慧,胡椒可入藥其實不用本草來提點至少我老媽也知道。小時候她給我十塊錢銅板,要我到存仁堂買五塊胡椒,餘下的五塊錢當然不能全算到我的走路工,化個一塊錢買根冰棍解解饞消消暑也是可以的。我問老媽為什麼不到雜貨鋪裡買,老媽有交代,國藥房的胡椒好、香,又便宜。可見我老媽雖然不識字不曉得本草是個什麼東西也還曉得生活花用一切從儉的道理。
連著看了兩本李國文的雜文或說讀書筆記,有點吃不消。我有個朋友很擔心我讀書寫字走上偏激一路,她擔心我好的不學盡學些中國文人的酸氣腐氣頭巾氣,李敖我覺著倒好,李敖這位本家我看倒不太好,大概朋友口中的酸氣就像我前引的這些文字一樣,透著股發酵過了頭的味兒。
要說李國文是有唸過書的,他的學問甚至不比正火的那個品東品西品簫品三國品六朝的易大天來得壞,自然也比那個錯漏百出古語今詮的于小丹來的高明許多,《長安成鬧鬼》裡面提到中國文壇怪現狀我都自動對號想成此二人(以下略三十數人)。可惜人家不待見、讀者不買帳,李國文的詞氣也就越見鋒利、酸氣也就越見衝天。
不信?我再抄一段。
韓愈和皇甫湜這兩位大師,親自登門去看望一位無名小輩,讓我感動。並非我厚古薄今,現在要找這樣虛懷若谷、提攜後進的文壇前輩,還真是難尋難覓。倒不是今天的中國沒有韓愈和皇甫湜這樣的大作家、名作家、老作家。可是,由於他們太忙於炒作自己,太忙於追求不朽,太忙於螢幕作秀,太忙於應酬飯局。更何況所到之處,左有美女作家,右有漂亮女記者,婷婷嫋嫋,我見猶憐,鶯鶯燕燕,春光無限,那雙眼睛忙得不可開交,因此,來不及禮賢下士,顧不上樂於助人,也就只有請大家原諒了。
我始終懷疑,這是不是多年以來中國文壇出不了李賀這樣才華蓋世的文學家的原因;同樣,我也懷疑,這是不是多年以來男過半百,鬍子一把,女已更年,仍在裝嫩,還要頂戴著青年作家這個冠冕的原因。
李賀的最後一句「他日不羞蛇作龍」,寄寓著他對未來的期望和毫不氣餒的抱負。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詩歌成就,其才思之靈動,其文句之奇麗,其創造力之光怪陸離,其想像力之汪洋恣肆,其在詩歌領域中獨開門派的先聲奪人,甚至超越了兩位前輩。
這位天才詩人,死年二十七歲,或曰二十四歲,還不到今天共青團員的退團年齡,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青年作家。由於早年受到韓愈破格的禮遇,並不遺餘力地獎掖鼓勵,因之魚躍龍門、聲聞九皋。看來,一個剛出頭角,尚未崢嶸的後生小子,是很需要有前輩指點和扶持的。確如韓愈在《雜說》中所言:「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就非常有道理了。
時下那些正在奮鬥的,「他日不羞蛇作龍」的,有遠大志向的青年作家,若是指望著寫得未必有上述大師好,但是架子之大、眼眶之高、自戀之甚、熱炒之忙,超過上述大師者,來做你的伯樂,那就無異於一個緣木求魚、守株待兔的傻瓜了。
這就使我們不禁要羨慕李賀的幸運了。
〈李賀與《高軒過》〉‧長安城鬧虎‧頁197‧李國文


王小波生年自然算不上青年作家,死時也活了李賀有兩倍歲數,他的文壇外一匹狼形象差堪與李賀早夭又才氣縱橫可相比擬,自然要夾帶一下。
抄得長了點了,我先聽個歌回來繼續說。沒閑,我先作個小結。要我說,雖然那個朝代都有些光怪陸離的,就連大唐盛世氣象也自不能免,但一個讀書人耙梳古文如果只是這樣小鼻小眼界,我說這叫做中國文人的非正常酸氣。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